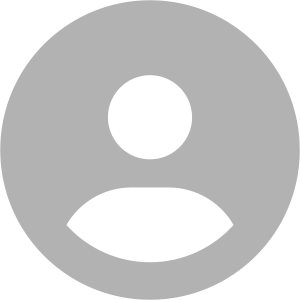台灣核電廠要延役所面臨的另一個巨大挑戰,是核廢料的去處與最終處置。
雖然台電在2004年時便提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並於2006年核定,其中指出預計在「2055年完成處置場之建造」。然而迄今為止,台灣關於用過核燃料棒最終處置的相關法源都仍是一片空白,直到2025年初才經濟部正式成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並預計展開高階核廢料選址辦法的立法。在此之前,台灣的高階核廢料都如何處置呢?
一直到2024年5月,核一廠室外乾式貯存場才正式獲得新北市政府核准,並在該年10月時迎來台灣核電史上第一次的「燃料棒吊離燃料池」,核二廠的室外乾式貯存設施也在同年12月底正式開工。在此之前,台灣3座核電廠的用過燃料棒都無處可去,只能就地存放於核電廠的燃料池中。
台電公司副總經理許永輝表示,目前核三廠的室內乾貯尚有待屏東縣政府同意,而且從施工到獲得執照整個流程可能需要花上7年之久。而核安會在2024年7月時曾指出,核三2號機的燃料池所剩餘之空間僅能讓核電廠繼續運轉約4年多。
換句話說:台灣要延役既有核電廠,首先需要解決核廢料處置的問題。核廢料處置不僅是空間的問題,同時也與核電的真實成本息息相關。
全球核廢料的處置困局
在各種核廢料中,最為棘手的用過核燃料棒具有高度放射性,需耗時數百年至數十萬年才能讓輻射回歸背景值。針對用過燃料棒的處置雖然有「再處理」的選項,但由於核廢料再處理技術高度昂貴且依然會產生高放射性核廢料,因此仍然需要有「最終處置」(final disposal)方案。許多國家所採取的作法是「深地層處置」(deep geological disposal),簡而言之就是將用過燃料棒放置於密封的鋼桶中,並將其深埋於「地質穩定」的地底深處。
目前全世界除了芬蘭的安克羅核廢料貯存庫(Onkalo spent nuclear fuel repository)之外,尚未有其他成功完工商轉的高階核廢最終處置場。安克羅貯存場從1980年代展開選址與地方溝通程序,2005年開始興建,預計於2026年啟用,僅僅是興建成本便耗資將近9億歐元,預估到了2120年時,其營運成本將約達到33億歐元。

安克羅貯存場是全世界少數接近營運階段的案例,其他國家不論是在興建進度或成本上都遭遇到不小的障礙。例如美國的育加山(Yucca Mountain)貯存場在1987年被選定為高階核廢最終貯置場址,但由於選址時未取得地方共識,因此在數十年期間中不斷遭遇地方抗議,再加上潛在的地下水汙染爭議等,該計畫在2010年時被中止。育加山計畫原初的估計興建、營運成本為960億美元,直到2022年時已經投入約150億美元在選址、研究、基礎工程、證照申請與審查等項目之上,然而當前由於計畫中止的緣故,缺乏後續的資金投入,完工之期可說是遙遙無期。
以台灣目前連高階核廢處置立法都才剛起步的狀況來說,要能夠走到最終處置場完工商轉的那一日,充滿了高度的不確定性,更遑論精確掌握究竟需要投入多少資金。恰恰由於核廢料的處置是如此地困難且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它是另一個可能劇烈影響核電成本的因素。
核能不是便宜能源選項:延役背後,是更難解的核廢風險
如前所述,核燃料後端處置之成本目前乃是由台電逐年提撥至「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支付,基金用途涵蓋除役、用過燃料貯存與最終處置等,至2025年為止足額提撥完畢。根據2023年核定版本,核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為新台幣4,774億元,其中用於「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約為新台幣1314億元,佔整體27.5%。然而,核後端基金所評估與提撥的這些費用,是否真的足以因應台灣6座核能機組運轉40年後所產生的高達4,731噸(tHM)用過核燃料棒?我們認為此數額恐怕仍過度低估核廢料處置的困難與成本。
以日本為例,根據日本原子能機構(NUMO)分析日本核廢料進行深地質處置所需的全生命週期成本,包括技術開發、場址調查、設計建造、運營、監測以及最終封閉等費用在內,日本的高放射性核能廢棄物的最終處置費用在2023年時估算高達3.36兆日圓,如今換算約為新台幣7,740億元。截至2023年時日本用過燃料棒的總量約為1萬9千噸,換算下來日本投注在高階核廢最終處置上的成本約為每公噸3,900萬元新台幣。反觀台灣則是每公噸的用過燃料棒處置費用為2,600萬元新台幣(以4,731噸用過燃料棒與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費用新台幣1,314億元進行計算),顯然台灣在核廢料最終處置的成本上有低估的風險。
更何況,台灣目前的高階核廢料尚未完成立法,預定場址與社會溝通則預計最快2028年後才會有所進展。考慮到台灣的地質條件與人口密集度,在核廢料最終處置上的成本恐怕只會更高。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總監趙家緯過去曾經以國際上核電除役與核廢料處置的成本計算,指出台灣當時所預估的核後端營運費用大幅低估。以核廢料最終處置為例,國外案例中的成本是以「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營運40年、監管300年」來計算,而台灣最終處置場的運轉時間則規劃為26年,如果按照國際標準,則最終處置費用可能超過新台幣2,500億元,整體後端營運基金規模至少應達到7,160億元新台幣才足夠。
核電如果要是個便宜的能源選項,最起碼的條件是核電廠必須能夠維持穩定的運轉,然而以台灣目前的狀況來看,核廢料的問題一日無法解決,用過的燃料棒便只能暫時性地存放在空間有限的燃料池中。中期貯存的選項如乾式貯存也同樣需要面對地方反對、耗時興建的問題。最壞的狀況就是花了大筆金錢讓老舊核電廠延役,額外創造更多核廢料之後,最終依然因為燃料池爆滿的原因而必須停機。
如果台灣的老舊核電廠要繼續延役,則既有的核廢料勢必會持續增加,因此「核電延役」絕對不會是毫無代價的低成本方案,而只是持續增加未來核電除役與核廢料處置的風險。

認識核電真實成本,避免落入核安與財政風險
綜觀本文所揭示的國內外案例與數據,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核電延役」對台灣而言,絕非一條便宜且穩妥的選項。
支持者主張延役可壓低發電成本,但實際上,台電所公布的核電成本嚴重低估了維持老舊核電廠運作所需面對的種種風險與財務壓力。首先,老舊核電機組必須投入鉅額資金進行安全設備的全面汰換與強化,以符合福島事故後國際普遍提升的安全標準,而這些升級常常需要多年審查,考慮到核三場周邊的斷層疑慮,甚至最終可能無法通過,導致巨額前期投入化為泡影,延誤了其他更為重要的能源轉型基礎建設。倘若勉強通過延役審查,斷層帶上一座服役超過40年的老舊核電廠,為台灣帶來的恐怕不僅是「表面上的廉價電力」而已,更是隨時可能引爆的核安危機。
其次,核電的真實成本還應包括核燃料後端處置的龐大不確定性,特別是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問題。目前台灣連用過核廢料最終處置的選址與立法工作都尚未完成,更遑論啟動實質建設。國際經驗如芬蘭與美國的例子已證明,高階核廢的深地層處置是一項動輒需數十年至百年、總成本以數千億元計算的長期工程,台灣目前的後端基金規模,恐難以支應真正所需支出。在尚未解決核廢料的問題之前,倘若貿然作出延役決定,無疑將進一步增加核廢料產生量,進而加劇當前用過燃料棒儲存空間不足的問題,並可能導致核電廠提前停機,所謂的「廉價潔淨電力」恐怕連一度都發不出來。
當我們以更長遠與更全面的視角審視核電延役,勢必會發現其背後隱含的龐大安全風險、財務壓力與環境代價,遠遠高於表面上的便宜電價。若執意延役,無異於以當下短期的能源成本穩定,換取未來數十年難以承擔的核安與財政風險。因此,台灣應慎審此一選項,避免落入「延役一時,貽禍後世」的代價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