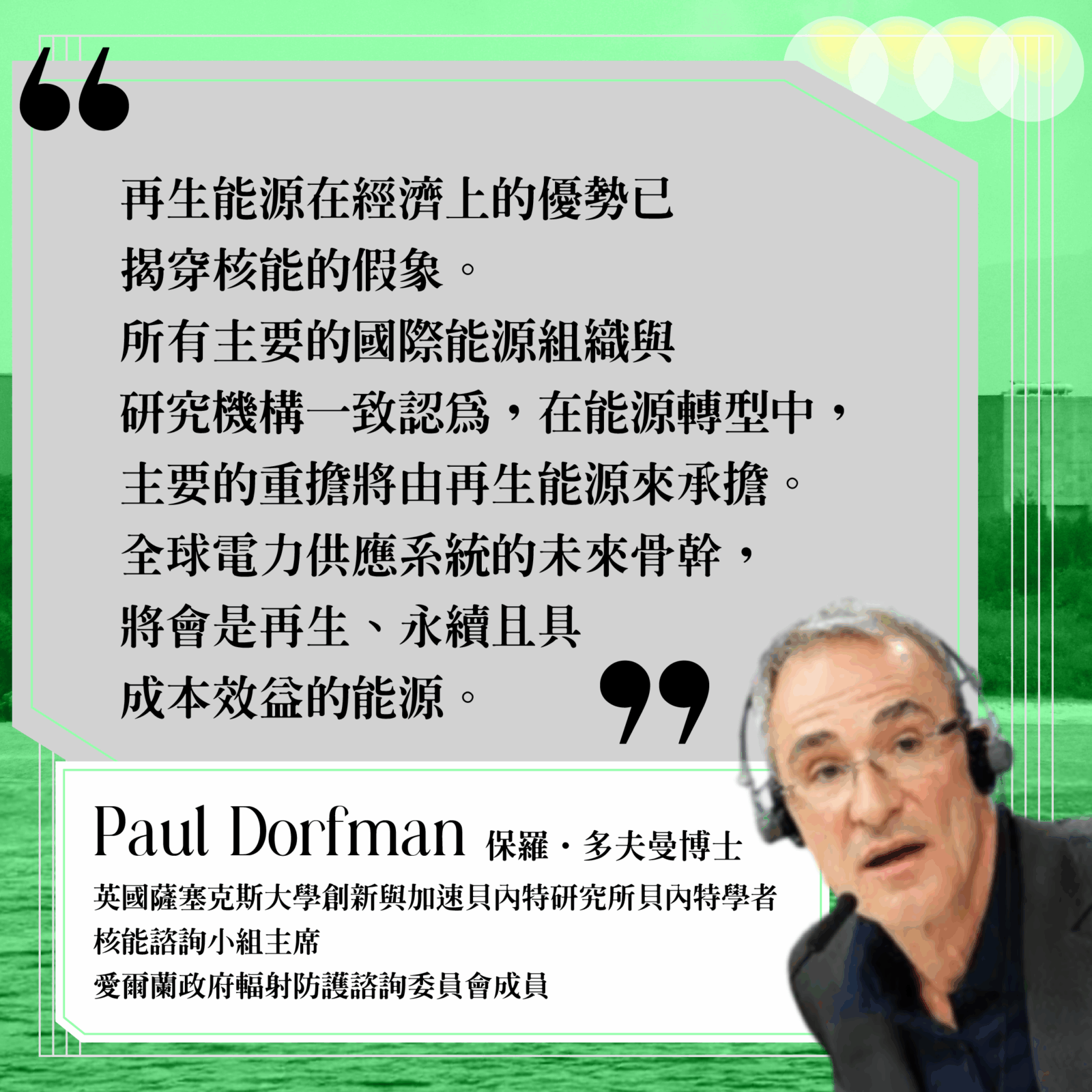台灣最後一座核能反應爐的40年運轉執照於今年五月到期,進入除役階段後,將於8月23日迎來馬鞍山核電廠(核三廠)是否應在「經主管機關同意確認無安全疑慮後」重啟運轉的全國性公投。為提供台灣選民當前最先進的科學知識與國際能源轉型的最新資訊,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特別邀請九位能源領域的國際專家學者,就本次公投中各方關注的「核電復興是否為國際趨勢」、「老舊核電延役風險」、「核電與國安」以及「核電是否可作為氣候解方」等關鍵議題,提供其觀點供全國民眾思考。
【日本「返核」不值效法,台灣續做能源轉型希望之燈】
日本永續能源政策研究所 飯田哲也 所長
台灣決定邁向非核未來,對東亞而言是一盞希望之燈。這是符合理性與邏輯的判斷,契合全球邁向 100% 再生能源的歷史性能源轉型。我們在日本由衷地表達支持。
相較之下,日本雖曾釀成全球最嚴重的核能事故之一,如今卻退回親核立場,實在不值得效法。這種倒退僅是「核電村」的產物——一個深植於日本政治核心、固守過時教條的親核既得利益集團。
日本核能政策的現實是完全的僵局,具體表現在:
- 東京電力公司(TEPCO)對福島第一核電廠提出的「40 年除役」計畫完全不切實際。
- 因此,東電以現有形態繼續生存已不可能。
- 六所村再處理廠與整個核燃料循環計畫在制度、技術及經濟層面上都已明顯失敗。
- 談任何「核能利用」之前,必須先有明確路徑與社會共識來解決核廢料處置問題,但目前完全不存在。
- 將所謂「淨化」後(實際仍高污染)的土壤分散至全國各地,扭曲了歷史上已建立的輻射安全科學與倫理。
另一方面,以 100% 再生能源為基礎的未來,在全球各地都能實現,包括台灣與日本。太陽能與風能的效能不斷提升、成本持續下降,加上儲能設備與電動車的加速普及,不僅能避免氣候危機,還能增進全球能源獨立,降低因石油爭奪及核戰威脅引發衝突的風險。
這場轉型將賦能於各地區與個人,促進能源自主,並催生永續且民主的社會。
台灣選擇逐步淘汰核能,是對未來的明智投資。我們全心全意支持這項勇敢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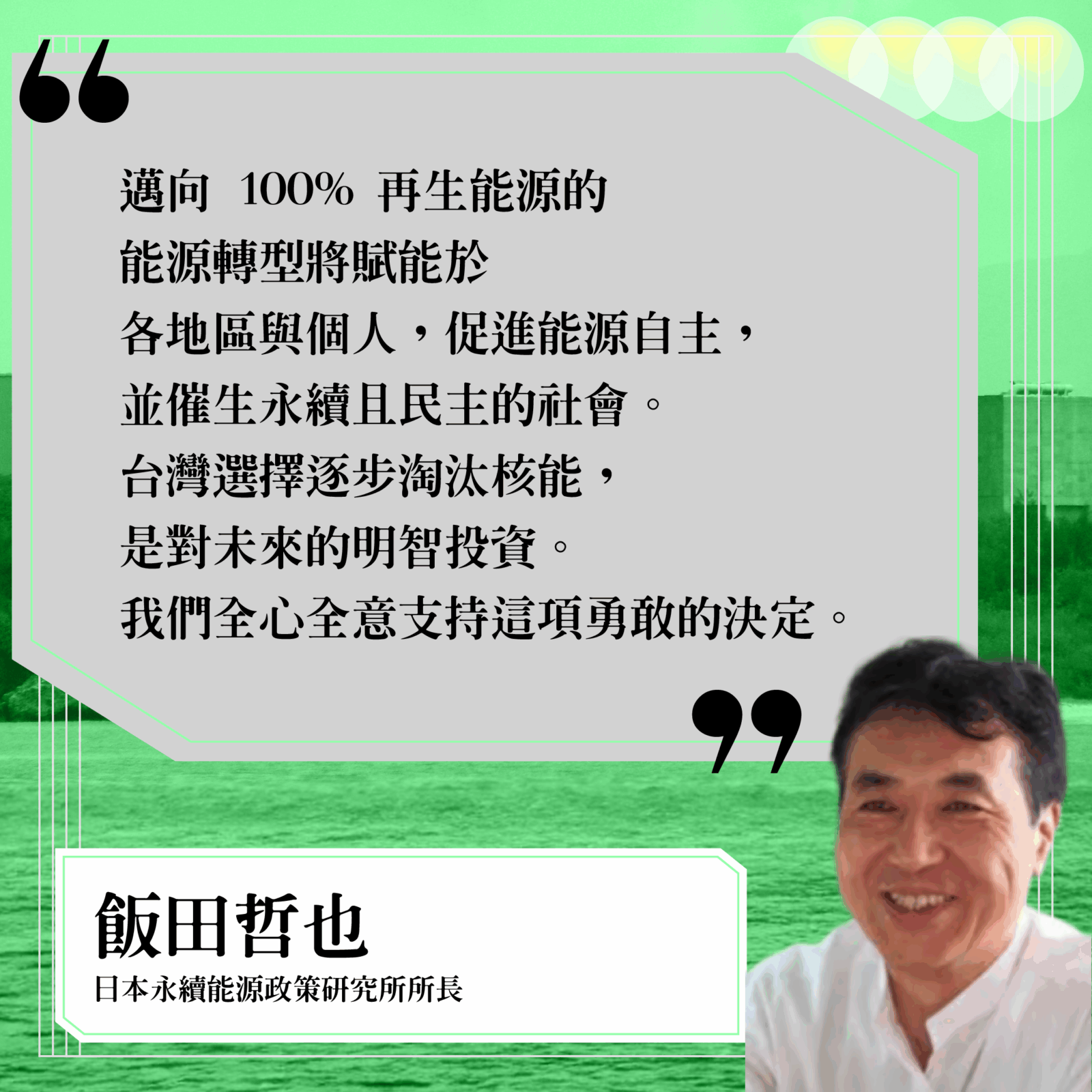
【日本維持核電政策的非理性與背後的真實原因】
日本東北大學 明日香壽川教授
2025年7月19日,關西電力宣布計畫在美濱町的美濱核電廠場址內新建一座核電廠。顯然,這項宣布特意選在參議院選舉最後階段(投票日為22日)進行,以避免成為重大新聞。
日本在2011年3月東日本大地震及隨後發生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中,僅以些微差距逃過了一場可能迫使數千萬東日本居民撤離的災難。然而,福島的重建停滯不前,至今仍有數萬人無法返回家園。
福島第一核電廠除役進度也遠遠落後。近期在7月29日,東京電力宣布,原計畫在2030年代初開始的三號機熔融核燃料(燃料碎片)全面取出作業,將延後至2037財年或之後。原因是方法檢討顯示,準備時間將比原預期多出12至15年。如今,幾乎不可能達到東電與政府所設定的2051年完成除役目標。
目前,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美國能源部以及多家投資銀行與研究機構的分析,新建核電廠或重啟(延役)現有核電廠,在發電成本與減碳成本兩方面都比再生能源昂貴。因此,從經濟理性與氣候政策的角度,全球正選擇再生能源。2024年,全球新增發電裝置容量中有92.5%來自再生能源。
換句話說,核電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事實上,在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自2017年初至2024年底,僅新增了四座反應爐(英國兩座、韓國兩座)。其中,英國Sizewell C核電廠的一座反應爐建造成本已達190億英鎊(約3.8兆日圓),其中一半(約1.9兆日圓)來自政府補貼(11)。然而,相同的發電量以再生能源可用更低成本達成,且若將同等資金投入再生能源,減碳效益將是重啟(或延役)核電廠的六倍。
至今,日本政府對核電的補助金額是再生能源的數倍,且目前正考慮為核電新建計畫推出新的補助方案。政府估算每座新反應爐的建設成本約為7000億日圓,遠低於英國與美國的實際成本,這一數字明顯被低估,甚至可說是一種「漂綠」(greenwashing)。
這種政府對核電的偏袒政策,與全球趨勢背道而馳,不僅透過更高的電價與稅收加重了國民負擔,還延誤了有效的氣候行動。更不用說,核電天生存在安全風險與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等棘手問題。
因此,政府對新建核電與重啟計畫的支持是一項不理性的政策。那麼,日本政府為何仍執意走這條路?原因其實非常簡單,歸結為兩點:
- 既得利益
- 潛在的核武能力
關於第一點,在日本,不僅是電力公司,反應爐製造商、鋼鐵企業與工程公司也都擁有龐大的既得利益,並施加強大政治影響力。
至於第二點,雖然決策者鮮少公開談論,但現任首相石破茂在2011年福島核災後接受雜誌《SAPIO》訪問時曾說:「我們必須維持核電,以保留潛在的核威懾能力。」此外,2002年5月13日,時任內閣官房副長官的安倍晉三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也表示:「只要不超過自衛所需的最低限度,擁有核武器並不違憲。」
顯然,日本政界有人將維持核電與核武裝掛鉤。不幸的是,對這些人來說,經濟理性、日本憲法與「非核三原則」都毫無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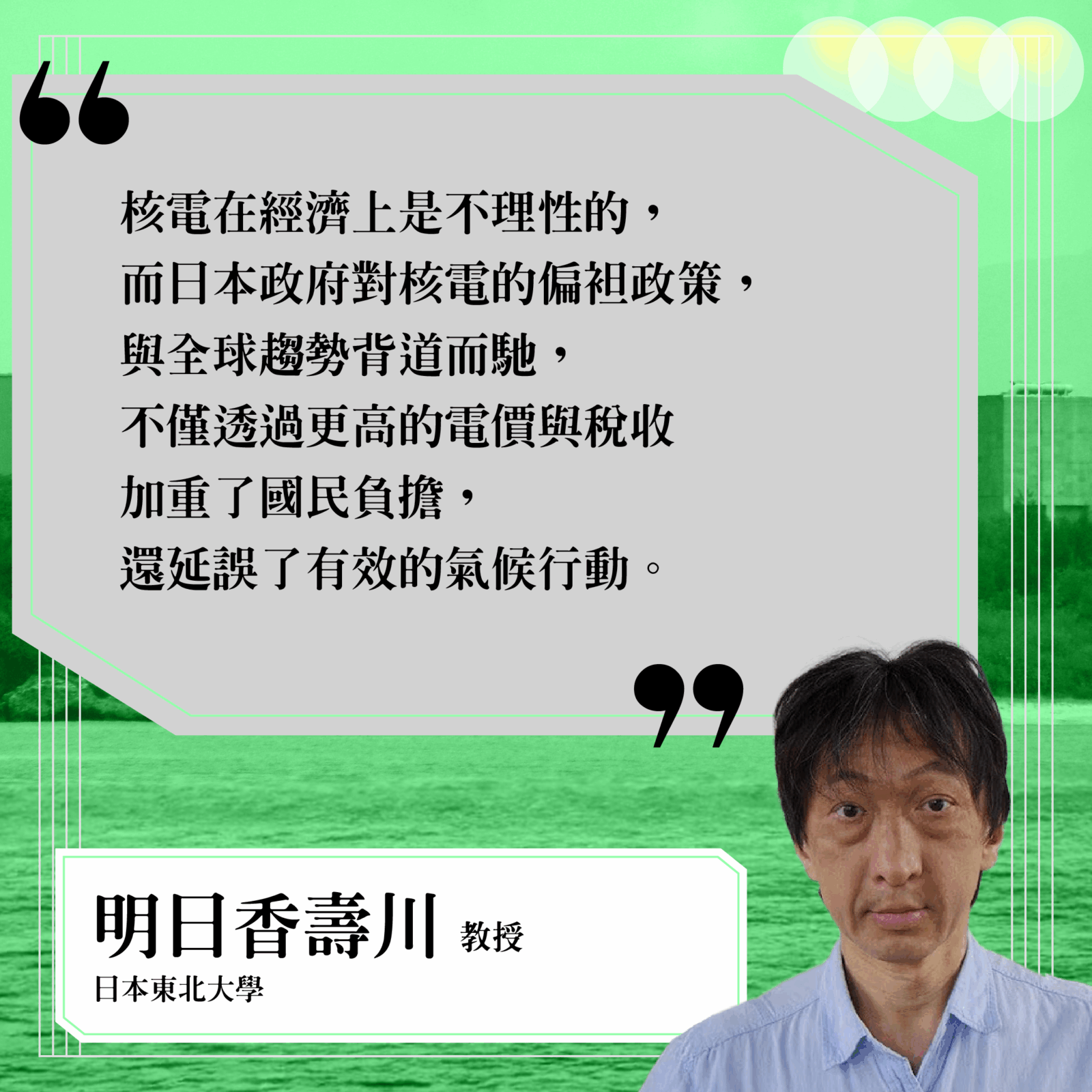
【亞洲第一個廢核國 台灣不須走回頭路】
首爾大學環境研究院院長 尹順真教授
台灣創下歷史紀錄,成為亞洲第一個廢核的國家。即使在正式政策決定之前,台灣就已經停止了龍門核電廠兩座幾近完工反應爐的建設。隨後,台灣於2016年做出了大膽的非核承諾,並擬定了明確的時程表,計畫於2025年前永久關閉所有六座運轉中的核反應爐。總計,有八座核反應爐從台灣的能源未來中被移除。這項成就不只是全球性的里程碑,更彰顯了台灣人民的智慧與決心,也展現出民主領導與公民參與在能源政策上的力量。
作為一名韓國的教育者與研究者,我長年支持台灣的反核運動,曾走遍台灣各地分享首爾市「一座核電廠減量計畫」的經驗。我親眼見證了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深受社區組織、資訊傳遞與動員過程所啟發。這一切都確保了能源決策不會僅由技術官僚或企業主導,而是由人民共同參與。台灣的經驗成為亞洲許多人心中的希望與驕傲,證明了即使在電力需求成長、仰賴進口化石燃料、再生能源仍在發展階段的社會中,仍可實現以正義與公民參與為本的能源轉型。
台灣的非核家園不只是一項政策,更是人民為未來做出的集體選擇。我們不應該走回路。讓台灣再次引領前行。
但如今,這項進展正面臨威脅。台灣的在野政黨發起了一項全國性公投,欲重啟最近才關閉的最後兩座核反應爐。8月23日,台灣人民將被要求投票決定是否要推翻這項經由長期努力才完成的非核轉型。正因如此,我寫下這篇聲明,不只是為了表達憂慮,更是要向台灣傳達國際社會的聲援。
儘管核能常被描述為對抗氣候變遷的低碳工具,現實卻更為矛盾:「氣候危機本身正逐漸削弱核能作為能源選項的可行性。」隨著危機惡化,海水溫度上升降低了反應爐的冷卻效率;極端氣候事件,如颱風、野火與因海洋暖化而暴增的水母群,也日益威脅核電廠的運作。更何況,在多颱風與地震的區域裡,災難的風險永遠都近在咫尺。最重要的是,核能產生的放射性廢料至今尚無國家能提供安全、長期的處置方案。
與此同時,台灣在擴展太陽能與離岸風電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貴國已經開始走在一條具韌性且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能源未來之路。若現在選擇回頭,不僅在科學與經濟上不智,更會動搖引領台灣至今的公民精神。世界正注視著台灣。你們曾經引領潮流,如今也能再次領航。
請堅持走下去。一個非核的台灣不僅是可能的,而是已經在實現的路上。我們不應倒退,而是要一同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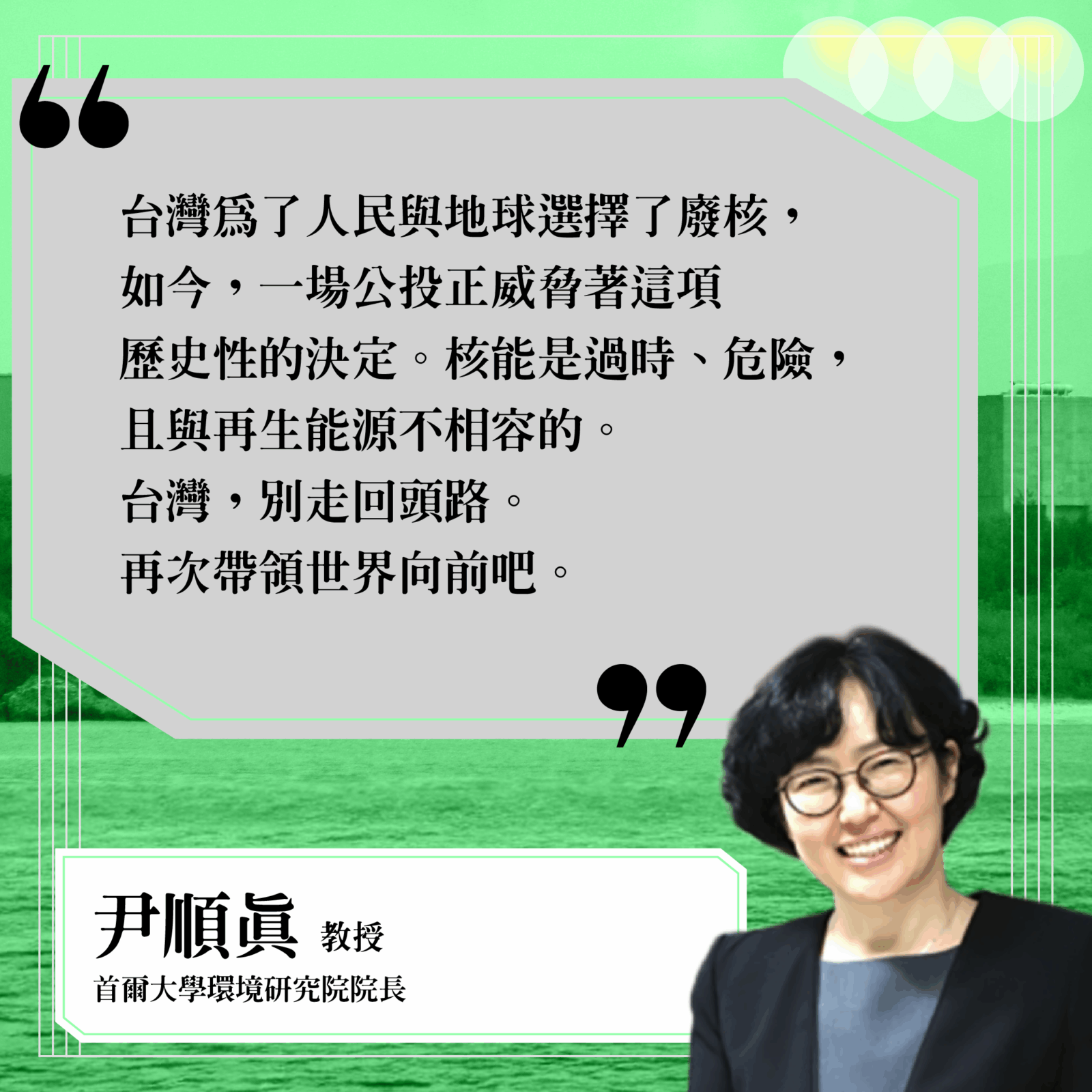
【老舊電廠風險重重,核能無法成為氣候解方】
MV Ramana 教授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公共政策暨全球事務學院 教授;西門斯基金會裁軍、全球與人類安全計畫主持人)
老舊機組隨著設備老化所帶來的相關磨損開始增加,故障率又會再次上升,增加反應爐運轉的危險。而正如烏克蘭車諾比1986年的事故和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等案例所示,核能事故的後果是災難性的,而且帶來長遠的影響和極其高昂的經濟衝擊。
台灣目前正就已停機的核能反應爐是否應重新運轉進行辯論。若要重啟,將帶來諸多風險,且無助於減緩氣候變遷。
核電廠延役的風險
隨著核電廠的老化,其發生事故的風險就越高。反應爐發生故障的可能性通常會用「浴缸曲線」來描述——在初始階段,新技術的製造問題和操作員失誤會使故障率較高,之後會隨經驗累積而像浴缸彎曲一般下降。但隨著設備老化所帶來的相關磨損開始增加,故障率又會再次上升,增加反應爐運轉的危險。而正如烏克蘭車諾比1986年的事故和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等案例所示,核能事故的後果是災難性的,而且帶來長遠的影響和極其高昂的經濟衝擊。
核能非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
核能是發電成本最高的方式之一,因此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核能發電在整體電力中的占比持續降低。如果核能真是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其比例理應上升,且化石燃料的比例必須下降,但現實並非如此。投資成本較低的低碳能源,能帶來更高的減碳效益。此外,建設一座核電廠約需十年時間,若加上取得環境和安全許可、獲得鄰近居民的同意、籌募龐大資金等籌備階段,整個流程將需15至20年。這樣的進度與氣候科學對緊迫性的需求不符。因此,核能在氣候變遷評估的兩項關鍵指標上均不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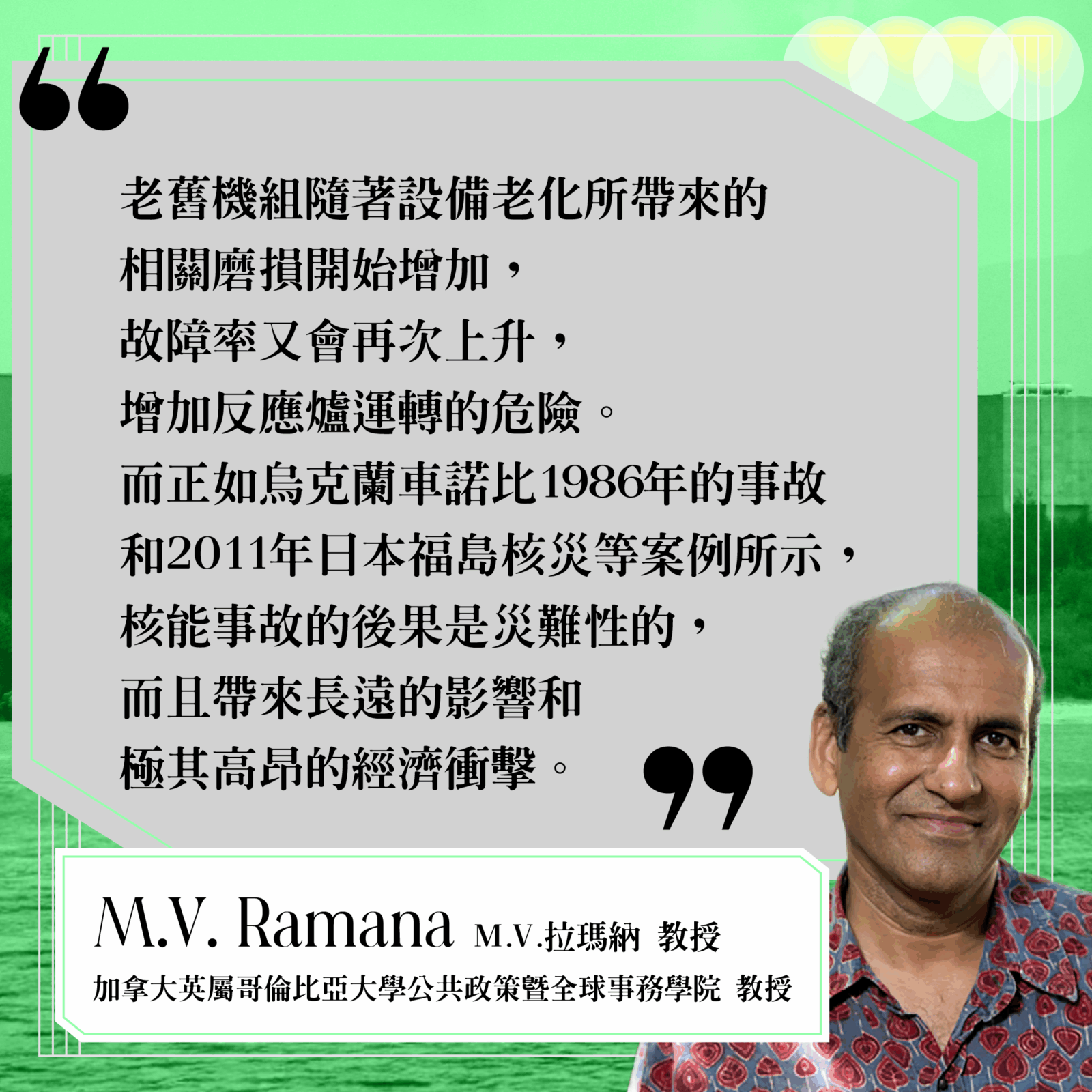
【光電貪腐不代表應該「返核」—支持台灣走向低碳非核之路】
Benjamin Sovacool 教授
(波士頓大學全球永續發展研究所(IGS)所長、英國薩賽克斯大學能源政策教授)
揭露光電市場的腐敗,是希望以更具社會責任、制度更完善的方式推動太陽能發展,並將其分散式能源特性的效益最大化——絕非號召各界拒絕太陽能,更不是以核能作為替代解方的理由。
在台灣即將舉行有關重啟最後一座核能電廠的全國性公投之際,謹以此聲明支持台灣的非核政策,以及加速邁向更具韌性、以再生能源為基礎的能源轉型。
據我所知,我近期所領導的一項關於加州光電市場腐敗模式的研究,已在台灣引發相當多的討論;但部分人士在公投前夕將研究成果曲解為對太陽能及再生能源所主導的能源轉型之唾棄。我在此必須明確重申,我們的研究呼籲的是以更具社會責任、制度更完善的方式推動太陽能發展,並將其分散式能源特性的效益最大化——絕非號召各界拒絕太陽能,更不是以核能作為替代解方的理由。
我過去數十年來已透過多篇論文指出,核能技術本身的特性以及長年苦心但始終未能實踐「核能復興」的核能產業,實與氣候危機下能源需求的應對方向背道而馳。其中幾項原因包括:核電廠的集中式特性,意味著龐大且昂貴的輸配電系統的需求;核能系統受限於對鈾資源可得性的高度不確定性,必須由技術官僚精英集中管理,且容易受到國際政治變動的影響。
相較之下,尤其是在台灣所面臨的各種挑戰中,綠能技術可降低對外國燃料的依賴,打造更安全的燃料供應鏈,減少外部經濟與政治變動的衝擊。它們也分散電力供應,因此停電時影響的容量較小,不如大型集中式設施的停電範圍廣。近用電端發電或儲能方案還能提升電力的可靠性,並減少需生產、運輸及儲存有害與放射性燃料的需求。
台灣能源未來的選擇,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是要回到一個由技術專家集中管理,完全依賴政府補貼,產生並分配核廢料,仰賴高度不確定的燃料預測,並且污染國家水資源與土地,長期破壞地球環境的核能經濟?還是要繼續走向一個儘管目前仍有缺點和一些轉型陣痛,但更有效率、將可獨立於政府補貼、商業可行、對環境影響最小、具備抵禦干擾與恐怖攻擊的韌性,並在適當治理下可讓所有世代及收入團體均享平等利益的分散式能源系統?
雖然能源系統的決策不是簡單的多選題,但在「返核」與「加速以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轉型」之間,答案也絕非「以上皆是」那麼簡單。我所主導的另一項研究,分析了全球123國25年來的碳排放與再生能源及核能電力生產,結果顯示,大規模投入核能技術的國家並未顯著降低碳排放,而再生能源卻有明顯效果;且核能與再生能源的規模呈現負相關,意即兩者在有限資源下往往互相排擠。
在避免氣候災變迫在眉睫,滿足日益成長能源需求挑戰艱鉅的當下,政策制定者與選民應看穿核能業界的煙霧彈,正視再生能源明顯的優勢和核能系統顯著的成本。面對氣候變遷,任何有效的電力需求策略都必須大幅擴大再生能源的運用,並穩健走向非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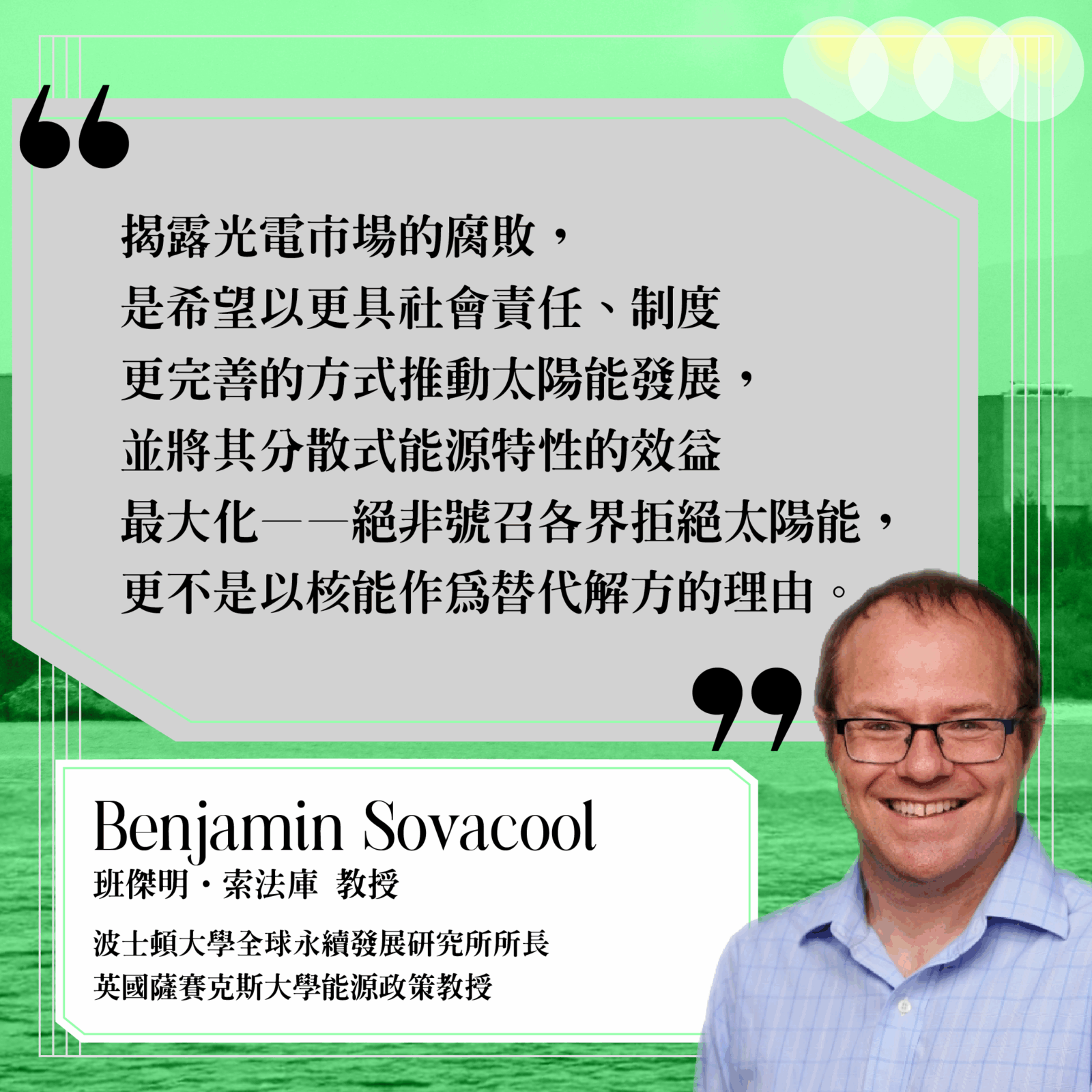
【綠能多重附加效益,加速轉型才是國際趨勢】
Sven Teske 教授(雪梨科技大學永續未來研究所研究總監)
能源的未來是再生能源
要實現《巴黎氣候協定》(2015年)的目標,全球能源系統必須在2050年前完全去碳化,並且在2020至2025年間達到排放高峰後迅速減少排放量,包含與土地使用相關的非能源類溫室氣體(GHG)排放也需大幅削減。
由雪梨科技大學永續未來研究所(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Futures)領導的「One Earth Climate Model(OECM)」研究計畫,清楚證明了巴黎協定的目標是可行且具實現可能性的,現有的高效能與再生能源技術足以達成這些目標,同時還能帶來經濟和就業方面的效益。這項研究成果對於負責推動國家與全球層級的再生能源與氣候目標的專業者,如氣候公約談判者、各級政府的決策者、具有再生能源承諾的企業、研究人員,以及再生能源產業本身。皆是必讀資料。
OECM 的1.5°C 去碳化情境是基於對所有形式的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技術的最有效運用,針對超過50個國家、地區以及全球範圍進行建模,以提供技術解析度高、並符合全球金融業使用的產業分類範疇之減緩路徑。
根據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最近的報告,再生能源依然維持了相對於化石燃料的價格優勢,這主要歸功於技術創新、競爭性的供應鏈與規模經濟。
太陽光電(PV)、陸上風電與離岸風電的電力平準化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預計將持續下降。太陽光電的成本已經下跌了90%,雖然這種急遽下滑的趨勢無法永遠持續;而陸上風電的成本也下降了70%。
— IRENA, 2025年5月
太陽能與陸域風力發電的優勢,不僅體現在減碳方面,還帶來了能源安全、能源公平、韌性等多重好處,並有助於許多國家偏遠與農村社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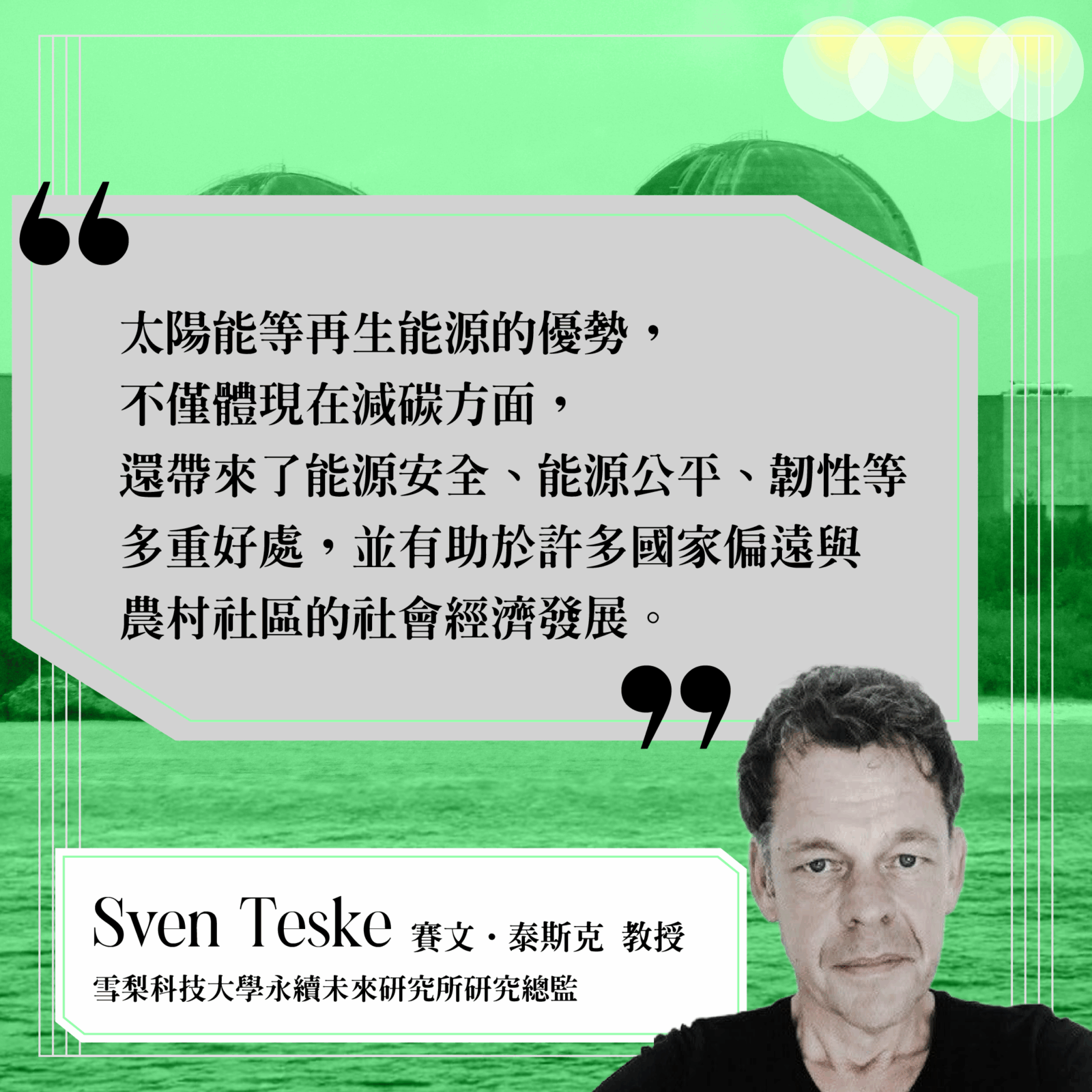
【德國經驗證實綠能未來可行、有利,台灣莫走返核回頭路】
Ortwin Renn 教授
(德國斯圖加特大學環境社會學與技術評估榮譽教授、德國波茨坦永續發展研究所(RIFS)榮譽科學總監)
我寫此信是為了表達對你們行動的全力支持——持續讓台灣的核能反應爐永久停運,並加速邁向再生能源轉型。這一立場不僅有科學證據作為基礎,也源於包括我所在的德國在內,一些已成功邁向永續能源未來國家的實際經驗。
2011年,我擔任德國聯邦政府「安全能源供應倫理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是在福島核災後成立,旨在評估核能在德國未來能源供應中的角色。經過與頂尖科學家、經濟界人士及公民社會組織的廣泛諮詢後,委員會一致建議:在十年內淘汰核能,同時大力投資再生能源。這項決策不僅是道德上的必要,更有堅實的經濟與技術理由支撐。
成果有目共睹——2011年至2025年間,德國電力生產中再生能源的占比由23%提升至超過54%,增幅達230%。2011年核能發電占比不到18%,而這部分電力早已被再生能源完全取代。此外,再生能源的擴張顯著減少了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為氣候保護與能源安全做出了貢獻。
如今,再生能源不僅潔淨,還具成本競爭力。風能與太陽能發電的成本已低於燃煤或燃氣發電,甚至在新設施建造成本計入後,也比核能發電便宜。確實,能源轉型需要在電網升級、儲能系統及備援方案上進行大量前期投資,但一旦基礎設施完善,再生能源長期的發電成本將低於化石燃料或核能。
德國相對較高的電價並非源於再生能源,而主要是受全球天然氣價格飆升以及進口電力成本影響。長期趨勢十分明確:再生能源正成為最經濟、最環保、政治上也最穩定的電力來源。
對台灣來說,教訓同樣清楚:向再生能源轉型是可行的、經濟可承受的,且最終有利於社會。它有助於氣候保護、環境品質與公共健康;它降低了對進口燃料的依賴,並避免了核能帶來的長期風險與成本,包括廢料處理及潛在的災難事故。最重要的是,它能促成去中心化且具韌性的能源系統,造福地方社區。
要達成這項轉型,需要大量投資與強大的政治意志,但德國的經驗已證明這既可行又有利。我強烈鼓勵台灣把握這一機會,優先選擇以再生能源為基礎的未來,而不是重返核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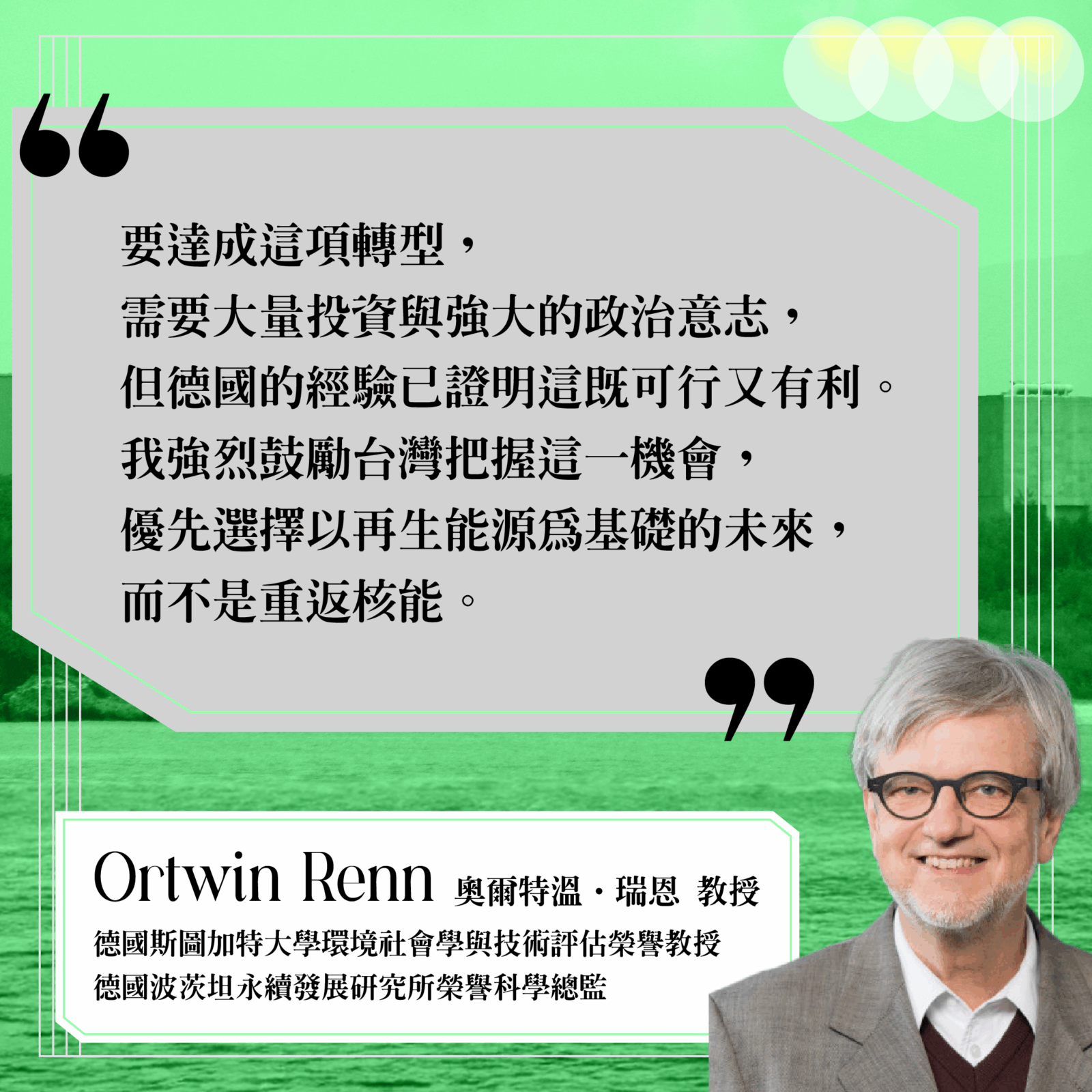
【緊抓核三不放,將排擠真正迫切的氣候行動】
Jan Haverkamp
(綠色和平(Greenpeace)核能與能源政策資深專家)
福島事故後的壓力測試揭示了台灣在地震情況下核能的巨大風險。「非核家園」政策是正確的選擇。
將核三發電廠升級以延長運轉壽命將非常昂貴。這筆資金更應投入到真正乾淨的能源轉型—更多再生能源、更多儲能、更好的電網,以及智慧化的需求管理。
「非核家園」政策是正確的選擇。只要持續落實,台灣就能成為東亞與太平洋地區能源轉型的耀眼典範。
緊抓核三不放是舊思維。真正乾淨、真正永續、真正高科技的解決方案——如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比這個食古不化的方案帶來更多、更快、更便宜的成效。核三所提供的電力太少,卻伴隨過高的風險與過高的成本。因此緊抓核三不放,會排擠真正迫切的氣候行動。
抱守過去並不能解決氣候問題。「非核家園」政策才符合前瞻性的能源轉型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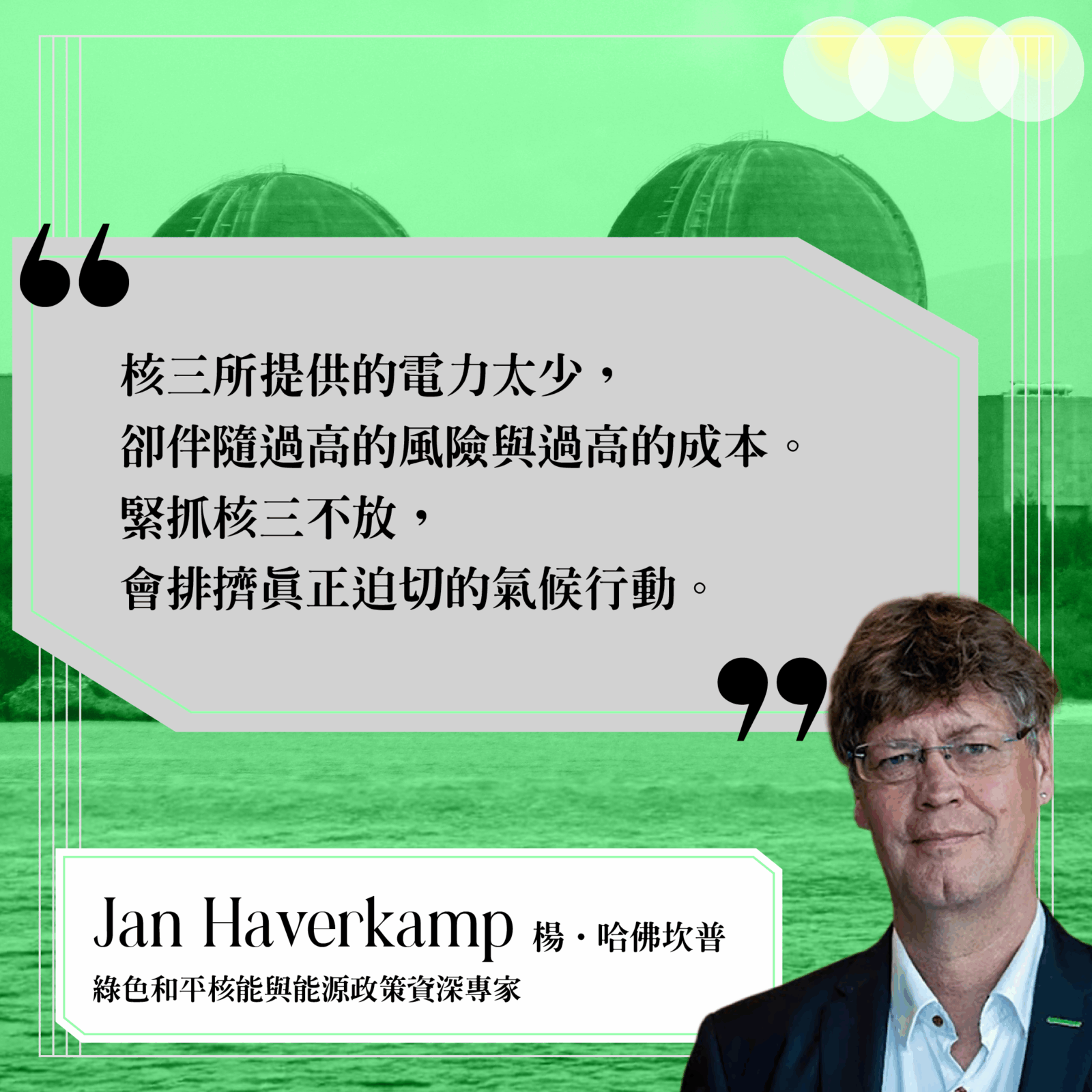
【綠能優勢揭穿核能假象,再生能源才是全球電力未來骨幹】
Paul Dorfman博士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創新與加速貝內特研究所(Bennett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Acceleration)貝內特學者、核能諮詢小組(Nuclear Consulting Group)主席、愛爾蘭政府輻射防護諮詢委員會成員)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率上,再生能源如今比新核能高出十倍。事實上,2024 年全球新增發電裝置容量中,有 92.5% 來自再生能源,新核能幾乎完全缺席。所有新建核電廠無一不嚴重超支且延誤工期。目前所提供的大型反應爐設計,是 25 年前的舊型號,本世紀以來並無新設計問世。至於所有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s)仍停留在設計階段,因此業界的預測必須持高度懷疑態度——而放射性廢棄物、核擴散以及廠址選擇等問題依然嚴重且未解決。
聯合國(UN)最新報告《掌握關鍵機會之窗》(Seizing the Moment of Opportunity)證實,再生能源的成本因規模經濟與廣泛部署而大幅下降。去年全球再生能源投資總額達 2 兆美元——遠高於核能。結果是全球能源系統新增了 582 GW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創下年增長率 15.1% 的紀錄,讓全球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提升至 4,448 GW。同時,國際能源署(IEA)報告指出,由於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低於化石燃料與核燃料,到 2030 年全球每年的再生能源新增裝置容量將上升至 935 GW。這些數據非常有說服力,且意義重大。
時間是減緩全球暖化的關鍵——而我們已所剩無幾。因此,選擇最快速、最務實、最具彈性且成本最低的發電方案,是完全合乎邏輯的。與新核能不同,再生能源已經成熟可用——準時完工且具成本效益。事實證明,透過在各領域擴大再生能源的應用、電網現代化與擴建、佈建儲能技術、加快區域電網建構,以及透過智慧能源管理更有效率地使用電力,是完全可以支撐一個可靠電力系統的。
當前正處於氣候緊急狀態,我們必須確保產業、交通、住宅與商業部門能獲得可負擔、低碳、可快速部署且經濟可靠的能源。我們擁有知識、技術與手段。再生能源在經濟上的優勢已揭穿核能的假象。所有主要的國際能源組織與研究機構一致認為,在能源轉型中,主要的重擔將由再生能源來承擔。全球電力供應系統的未來骨幹,將會是再生、永續且具成本效益的能源。